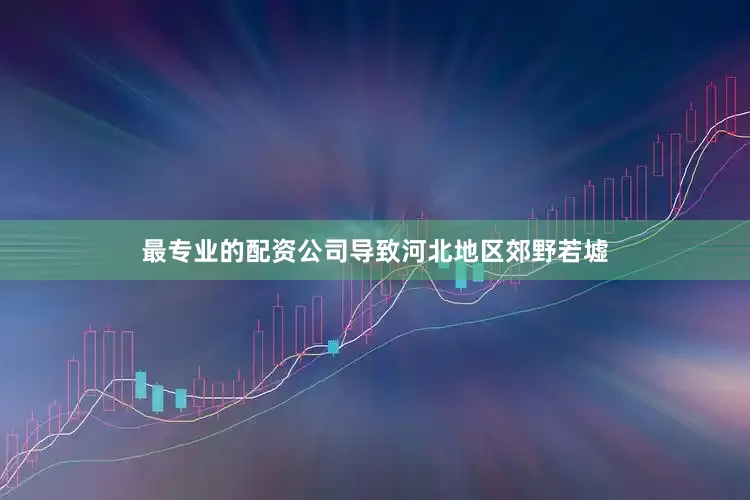
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,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。

面对毫无防守的水寨,耶律德光心下生疑,他就感觉这个地方越是看着没人,其实就越是有人,他就没敢再继续进军,干脆,他调转方向,又重新返回了战场。
得时无怠,时不再来,天子不取,反为之灾。
这么好的机会,竟然就这么硬生生的错过了。
更糟的是,耶律德光他往回走的时候,正好遇到了后晋将领李守超的一支军队,李守超看到耶律德光就打,契丹军刚刚结束一段追击,人困马乏,被李守超杀的大败。
那么总结来说,耶律德光调动全军,用各种办法想要突破后晋的防线,结果都是徒劳而已,收效不大,反而在这个过程中,契丹军的军力消耗巨大,又被李守超打了一顿,再战无力,无奈之下,只好鸣金收兵。
想不退兵,也没办法了,因为耶律德光此次南下,战略目标有三个,一是渡河,二是会师杨光远,三是在野外将后晋军主力消灭,结果这仨目标一个都没实现,反而是契丹军后勤枯竭,士卒疲惫,攻坚受挫,伤亡巨大,继续在澶州城下已无胜算,再待下去,那就是人家后晋军反攻了,到时候能不能走都说不定。
所以,耶律德光选择了退兵,但他不是单纯的退兵,他非常的不讲究,退兵途中,他毁坏城池,屠杀平民,掠夺财物,导致河北地区郊野若墟,白骨蔽野,社会环境和百姓的生活遭到了巨大的破坏。
但是无论契丹人如何泄愤,如何不满,他们都必须接受一个现实,那就是素来自恃武功天下无敌的他们,被他们曾经最鄙夷,最瞧不起的后晋军杀的大败。
二月份耶律德光撤军之后,十月份他在契丹国内过生日,在契丹叫做天授节,那个时候契丹的发展的非常的不错,何况在太祖阿保机时期,北方诸政权基本就已经都被征服了,所以耶律德光他过生日,各个藩国都会派使者来,有来道贺的,有来送礼的,以前后晋对契丹称臣,后晋比谁来的都快,可是现在不一样了,契丹新败,在后晋吃了亏,人家后晋已经明确和你契丹撇清了关系,你再想收后晋的礼,那是不可能了。
对于耶律德光来说,这是无法接受的,因为在契丹人看来,后晋完全就是契丹人创造出来的政权,更是契丹借以控制中原的这么一个傀儡,要么他俯首称臣,要么他就得飞灰湮灭,所以天授节刚刚过完,耶律德光立刻开始了第二次南侵。

这一次,打头阵的仍然是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,他作为先锋,围困恒州,契丹大军速度很快,在邢州,洺州,磁州也出现了他们的踪迹,甚至一大批契丹军已经进入河北大名一带。
当时负责恒州防务的,是后晋将领杜重威。
哎,还是这个关系户。
他呢,能力一般,面对契丹军的倾轧他难以招架,不过杜重威也不傻,打不过也不硬来,而是立刻向朝廷求援。
朝廷得知契丹人卷土重来,当下派出将领安审琦,张从恩,马全节去支援杜重威,几路后晋军集结于恒州,两方对峙,一场世纪大战是又要开打。
实际上,有了上一次的经验,这次打契丹人就没有那么害怕了,他们战无不胜的形象已经被打破,你来一次我打一次,你来两次,我打两次呗。
奇怪的是,我们翻阅史书,却发现了这样一条记载:
朝廷惮契丹之盛,诏从恩等引兵稍却。
什么意思呢?就是后晋朝廷审时度势,认为眼下契丹军的兵锋太盛,不宜开战,如果开战,很容易直接被契丹军一锅端了,被全歼了。
所以,后晋朝廷在仗还没开打的情况下,莫名其妙的下达了撤军的命令。
您知道士气这个东西是很玄妙的,如果朝廷说,将士们,我们共同生死,绝不退却,杀身成仁,就算纸面实力上后晋不是契丹的对手,那整个军队所展示出的风貌,那个气象,也是勇敢向前的。
而一旦朝廷怯战了,让士兵们撤退,士兵们心里的这股劲儿啊,这个勇气啊,一下子就没有了,所以后晋军在撤退的时候,他们是情绪低落,自乱阵脚,退着退着就开始丢盔弃甲,兀自奔逃,知道的这是退军,不知道的以为战败了呢。
不打就逃,这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了。
后晋军撤退到了相州一带之后,朝廷突然又反应了过来,说这不能再退了啊,这么主动放弃战场,万一契丹渡过黄河了怎么办?于是朝廷又开始把军队布防在澶州,邺都,黎阳,胡梁渡,安阳五个地方。
赵在礼负责守澶州,马全节负责守邺都,张彦泽负责守胡梁渡,安审琦负责守安阳。
最后后晋军和契丹军是在哪儿碰上的呢?是在榆林店,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方向。
当时,契丹的主力是骑兵,而后晋军的主力则是步兵,两军相遇,仓促开战,因为骑兵天生克制步兵,在这种兵种压制之下,后晋军一度落于下风,但是要说这些中原将士们,真的很可以,誓死不退,坚持抵抗,从中午十一点一直打到第二天的下午三点,血战一百余场,契丹人始终没能攻破后晋军的防线。
这支后晋军的将领,有两位,一个是皇甫遇,一个是慕容彦超。
两位老将军,深陷敌营之中,奋力厮杀,皇甫遇一个不小心,马失前蹄,从战马上跌了下来,他的仆人杜知敏赶紧把自己的马让出来给皇甫遇乘骑,皇甫遇这才脱离险境。
可是,杜知敏没了马,却很快被契丹人给俘虏了。

杜知敏被俘虏的时候,皇甫遇和慕容彦超已经突围出了险境,他们是可以暂时撤退的,但是皇甫遇没走,他感叹道:
《资治通鉴·卷二百八十四》:知敏义士,不可弃也。
杜知敏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,我不能这样抛弃他。
话罢,皇甫遇又杀入契丹军中,左劈右砍,终于又把杜知敏给救了出来。
真正的担当,是在他人为你牺牲时,选择成为对方的铠甲,杜知敏在五代十国历史上并不有名,诚如所见,他只是一个仆从,但是他把马匹让给皇甫遇的瞬间,他就深刻的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而皇甫遇选择回身救援杜知敏的那一刻,他也真正的成为了乱世中的一位名将。
有情如此,手足何求?
只不过,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,皇甫遇是把杜知敏救出来了,但是他这么一耽误时间,后晋军又落入到了契丹人的包围圈中,当即再度陷入苦战。
在后方驻守的安审琦一看皇甫遇和慕容彦超老半天没回来,他很着急,立刻对另外一个将领张从恩说,说皇甫和慕容两位老将军耽误了这么长时间还未折返,一定是遇到了契丹人的围攻,我们应该赶紧救他们。
张从恩皱着眉头说,如果他们已经被契丹军包围了,那包围他们的契丹军也必定是主力,咱们去又有什么用呢?哪怕把全部的兵力都送上去,恐怕也不是敌手。
安审琦大怒,他指着张从恩说,成功和失败,从来只看天意,就算不能取胜,同为将帅,也应该有祸同当,难不成你叫我在这里眼睁睁的看着自家兄弟战死吗?如果是那样,战争结束之后,我也没有脸面见天子了。
话罢,安审琦带兵直奔前线,终于击退契丹军,把皇甫遇和慕容彦超给救了回来。
至于张从恩,他不是认为去救皇甫遇,成功救援的概率很低,而是他压根就是怯战之人,因为现在契丹军已经被击败了,已经有颓势了,按理说应该乘胜追击,但张从恩却说自己兵力不足,粮草不济,他都没和大家商量,直接带兵就撤退了。
主帅一走,剩下的将士们更无恋战之心,纷纷向南撤离,一时间后晋军中是辙乱旗靡,弃甲投戈,在恒州城不战而逃的那一幕又上演了。
张从恩是撤走了,但是契丹军并没有撤走,他们还在观望,当时的相州刺史,名字叫做符彦伦,他认为现在情况混乱,人心惶惶,契丹人必然来攻,而张从恩已经撤军,相州城里只有几百士卒,根本就没有办法防守。
兵书有云:虚者虚之,疑中生疑,刚柔之际,奇而复奇。
为了应付契丹军来犯,符彦伦使了一招空城计,那就是他让相州守军举起军旗,擂鼓大喊,还要大声的传递号令,弄着整个相州城尘土飞扬,声势很大。

哎,耶律德光别的计他不中,他就爱中这种疑兵之计,他本来要带兵打相州,结果看到相州城里人头攒动,他就觉得城里肯定有重兵调动,就等着自己进去,好瓮中捉自己呢。
可是,此番南下,没有建树,耶律德光也不想回去,这哥们干脆绕过相州城,过而不打,继续行军,但是终究没有斩获,到最后还是只能大军全撤。
只有赵延寿,他当了两回先锋,就这么潦草收场,他实在是觉得脸上无光,干脆,他领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契丹军,摆到相州城下,他也学符彦伦,擂鼓三通,列阵号喊,意思就是我这可是契丹主力,大军兵临城下,还做出了马上要攻城的样子,他是要诈一诈符彦伦,要符彦伦在这种威慑下主动献城投降。
结果符彦伦根本不上当,坚守不出,赵延寿自娱自乐了一顿毫无斩获,也只能是悻悻退走。
这次北伐,契丹人又输了。
而且,输的很狼狈。
刚才我们说,皇甫遇和慕容彦超带的是主力,但其实说是主力,说的是他们的战斗力精良,而非人数多,实际上当时这支军队只有几千人,但却顽强作战,硬生生的拖住了数十倍于他们的契丹军。
但是,虽然取得了阻敌的胜利,但这一仗,也暴露出了后晋军的一个严重缺陷,那就是,后晋的将士们,战斗力高,作战能力强,可在战场上,他们缺乏统一指挥,难以协同作战,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联动,相互之间的情感纽带和同仇敌忾的心情更是薄弱,这也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笔。
天地英雄气,千秋尚凛然,事实上,一场一场的大战过去,大家都意识到了,契丹人并非不可战胜,不仅可战胜,还很容易战胜,但是,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太多了,在将,在兵,在地形,在天气,在粮草,更在人心。
契丹人的战略目标,是渡过黄河,攻陷后晋的都城开封,而打仗,有些时候就像治理黄河。
千百年来,封建时代的王朝们,一统的也好,割据的也好,大家都治黄河,但都没能彻底的治好黄河,不是黄河治不好,而是因为,治理黄河的关键不在于河,而在于人罢了。
至于到目前为止契丹人的惨败,也很有意思,也不在于他们的能力不行,指挥不行,而是因为,他们恃强凌暴,失道寡助,徒有武力而无德政,空怀野心却不懂“治人”之要。
他们视后晋为傀儡,视中原为牧场,所过之处“郊野若墟,白骨蔽野”,其暴虐,注定了他们无法真正征服这片土地...
什么是天下?
人心,才是天下。
参考资料:
《旧五代史·卷九十五》
《资治通鉴·卷二百八十四》
《百战奇法·卷第十》
王建平.论耶律德光.吉林大学,2011
郑毅,李鑫.汉族武装与辽初政治.辽金历史与考古,2011
专业在线股票配资交易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